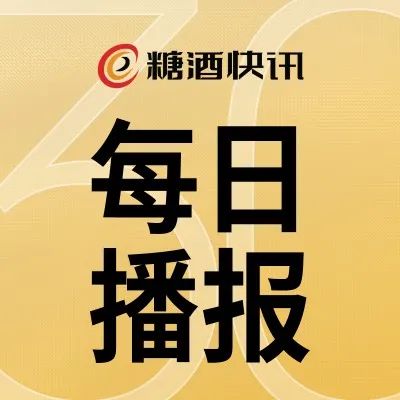仁商仁匠 | 欧杰:汉王的“大家长”


文 / 黄雪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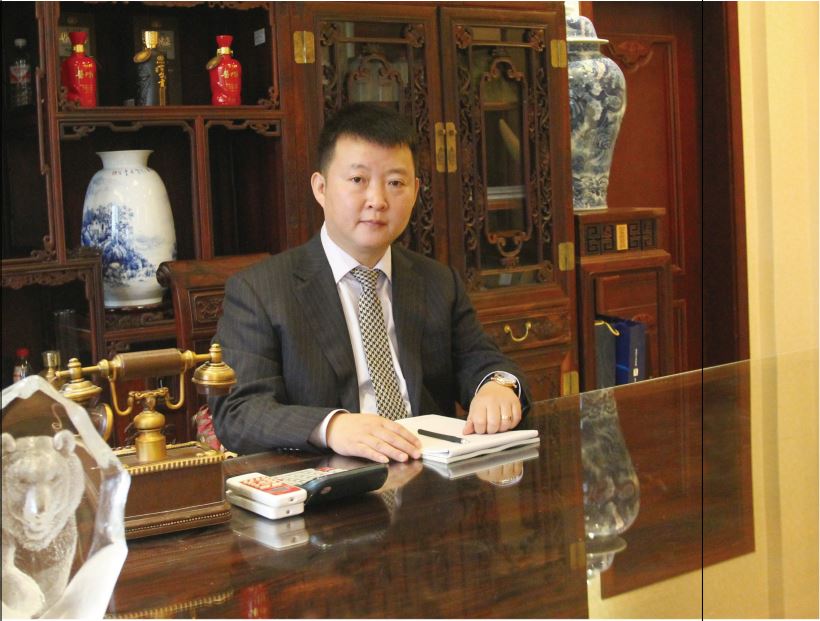
欧杰:贵州汉王酒业董事长
严厉的家长
每天凌晨四点半的时候,欧杰就已经起床了。驾驶员会准时在六点钟来接他,然后六点半到酒厂,几十年如一日。
除去工作日,欧杰周末也会到厂里加班。繁忙的日常,超强的工作量,他感觉有点吃不消。为了保证充足的睡眠,欧杰推了很多应酬,并在晚上八点半准时入睡。一到晚上八点,他电话就很难打通,“我要休息,不然身体受不住。”
身边的人说他“工作狂”,欧杰也这样认为。或许是自己太过用功的缘故,他总是觉得两个儿子还不够勤奋,“我对他们要求很严格,因为我是树立了榜样的。”
大儿子已经成家,没有和父母住在一起,去得比欧杰略迟,但八点半是必需到酒厂的。小儿子和他住一起,“我五点半就叫他起床,就跟我准时坐一个车上班。”
酿酒的温度高,若是酷暑天气,酒甑上了蒸气之后,周边温度高达四十度左右。酿酒工人大多习惯在凌晨四五点工作。欧杰父子到厂里的时间,也是烤酒季出酒的时间。
工人们烤完酒就下班走了,欧杰不能走。厂里所有的勾调、生产监督、包装,他都要亲自负责。一切亲力亲为,欧杰对酒厂一应事务,都了如指掌。“烧锅炉一天要用多少气,跟煤碳相比能节约多少,我都晓得。没有任何环节可以骗得了我。”

家长制应该是民营企业的一种普遍现象,欧杰正是一个典型的“大家长”。这种制度的一个好处是,当市场或政策发生变化时,企业能以最快的时间做出应对,效率极高,但一个弊端是,当一切集中于一人,就极为考验这个人的经验、能力。一个人的能力毕竟有限,而且,会很累。
每天都忙碌于酒厂的事务,欧杰很累,也早已感受到了压力,“我担子太重了,几百号人跟着我,但没有人能帮我。”
做酒不能急
欧杰是个急性子,急起来谁的面子都不给。“我经常跟人吵架,”欧杰说,“(大儿子)超过八点半(没到酒厂)我就要骂人,他不愿跟我在一起是怕我。驾驶员也怕我。”
或许有压力大的缘故,但这也是一代创业者的风格——为人处世强势霸道,做事又雷厉风行,极有决断力。他们很强大,但严厉的性格总让身边的人望而生畏。
欧杰似乎并没有感到不妥,又说:“我是说一不二。”
他却说做酒不能着急,“我是急性子,但在酒上急不得,做事业我一定得沉下心。我的想法也和很多人不一样,有的是想做大做全,我是把人、事、酒做好。”
欧杰说不着急是父辈给他留下一个丰厚的家底。那是1983年,欧杰的父亲和两个朋友凑了一万元,又贷了七千,就那样建起了酒厂。酒厂最早不叫汉王,是叫茅馨酒厂。过了几年,仁怀不允许民营酒厂带“茅”字,他们就改名叫做怀康酒厂。
怀康酒厂规模不大,只有二十几口窖池,且是小窖池,一口窖池大约能产出五六吨的酒,一年产能只有百吨余。
欧杰的父辈挣到人生的第一桶金,但在过了两年好日子之后,贵州白酒进入野蛮发展期,用当地人的话说,就是“发酒疯”。
后来,仁怀积压下大量白酒,很多酒厂也倒闭了。那是一个连茅台酒厂都为去库存而发愁的时代。到1988年欧杰接班的时候,另外两家人已先后退出,只有欧家人留下。欧杰的父亲交给他二十几吨好酒。
优质老酒是酒厂的魂,欧杰说他想用这些老酒,做“最漂亮”的酒。“不能太喜欢钱,太喜欢钱就要出错,所以底子厚最关键,不然吃不饱饭如何坚守底线?”欧杰说,“我家的积累在父祖辈就有了,所以我是不慌不忙的。”
当然,还有一个原因,是他尝到了做好品质的甜头。
上个世纪的八九十年代,是浓香的天下。那时的仁怀,除了茅台酒厂,大多酿的不是酱香,而是浓香。欧杰就说自己“很怪”,他是为数不多的,从一开始就只做酱酒的。

不做浓香做酱香,大约是因为酱酒出酒率不高,好酒率却很高的缘故。酱酒能保证品质,欧杰便从未改变过,“我做事很专一,对酱酒是情有独钟。”
酱酒的香味、口感独特,当时能接受的消费者便远不如浓香庞大,但对浓香或其他香型而言,酱酒却是很好的调味酒。他说接手不到五年,就有成都崇州、大邑、蒲江、温江等地的酒厂,到他这里来买酒,“川西一带没有不认识我的,他们是买酱酒去调。”
因为没有竞争,欧杰似乎也不愁销路。“我没有销售部门,就是我一个人搞销售。”听起来有点不合常理,甚至谈起购买对象还有几分神秘,但欧杰很笃定:“不是我有本事打天下,或者一家家送酒样,就是得到一个(做酱酒)的好机缘,然后去坚守,做好品质。(销售)我不需要做得很好,我只要把产品做好,就供不应求。”
话虽如此,到底是诸事集于一身,包括销售也是他自己上阵。欧杰累,不是没有原因的。
保守的汉王
正式接手酒厂,是在1989年。这一年的中国,经济发展陷入停滞,从过热走进低谷。很多仁怀酒厂的日子,举步维艰。
尽管欧杰走了一条和很多人不一样的路,但大势如此,酒厂当时的发展速度也远不如今天。用欧杰的话说,是“在1997年之前,都是不温不火的。”
他调侃汉王酒业是“三无企业”:除了无销售部门,还无官司、无贷款。他应该也是个保守的人,不向银行贷款,也从来没有考虑过,利用金融杠杆,迅速做大企业规模。
“没有欠钱、贷款,我的生意做得很舒服,这样多安逸。就算遇到行业调整期,我们也没有大的起伏,没有受过挫折,一直很安全,很平稳。”2014年前后两年,应该是行业的至暗时刻,但欧杰说他的汉王酒业依旧“风生水起”。
做企业总是要敢冒险,要有点赌性的,但“稳健”对企业而言,至为关键。毕竟,比起做强做大,企业最需要做到的是好好活着。活着,应该是熬过行业寒冬期的仁怀企业主们奉行的最朴素的真理,当然也是他们最大的体会。
汉王酒业一直在稳步扩产能。它现在约有五千吨的产能,有近三千吨是自建酒厂的产出,其余的产能,来自于租赁的酒厂。2010年左右,贵州提出“一看三打造”的规划,一时之间,仁怀再次疯狂,建设了大量的厂房。当2012年行业遇冷之后,新建的厂房、新扩的产能,大多偃旗息鼓,有的人便把厂房租借出去。仁怀很多酒厂都有租赁的厂房,既不影响品质,又能降低风险,控制很大一部分成本。
只是,酱酒起风之后,很多借出厂房的,开始考虑收回来自己酿酒。欧杰正面临着这样一个问题,而这也是很多仁怀酒企同样面临着的——当时代与市场发生改变时,若要维持原来的产能,他们或许需要付出更高的成本。

市场给仁怀带来的另一个改变,是资本的大举进入。借助资本的力量,很多酒企再次开始扩产,迅速占领市场。毕竟,白酒虽然整体在下滑,但酱酒一直处于上升趋势,而消费者也越来越理性,对品质的要求越来越高。
欧杰不为所动。“我走的方向、我的想法和别人不一样,目前还是按照我自己的思路来走,要静下心来做。我没有大的打算,就是守住底线,做好产品,做好质量,把风险控制在最低,让所有员工都能共同致富。如果孩子们有想法,今后也能独立承担事责任,那是他们的事情。在我这里,没有十足把握,就算资本再多,但只想捞一票走人的,我不会考虑。”
当然,他也补充道:“扩产也是对的,但一定要有资金、管理、团队的支持。现在也有来找我们的大资本,我也在考虑。如果资金、管理跟得上,大家志同道合,我们也可以合作,毕竟都想做大做强。”
如果时间还在去前年,欧杰的想法实在保守,但现在来看,保守一点更稳妥。
汉王的改变
欧杰看起来很保守、固执,却也有“出格”的时候,比如给酒厂改名字。
企业改名是大事,稍有不慎,便有可能伤害原有的形象,甚至影响发展。中国人又信命信风水,便是取个名字也要再三思量是否周全,不止要响亮要看寓意是否吉祥,还要看名字是否能旺家族与己身。生意人更甚。
欧杰酒厂换名字的因由过程,看起来竟有几分与常理不合了,甚至还带着几分随意——接手酒厂之后,他一直觉得父亲取的“怀康”二字,不够响亮。后来,一部叫《汉武大帝》的影视剧火了起来,欧杰便把酒厂的名字改为“汉王”。
这便是“汉王”的由来。不过,今天来看,“汉王”似乎确实比“怀康”更响亮。

如今,欧杰试图追溯汉王的历史。他时常在为十年前扩了老厂房而后悔,认为自己没有保护意识,没有保存好老厂房。和以前只知埋头酿酒不同的是,现在的仁怀酒圈,也开始注重对外的表达,包括酒厂的故事、历史。上个世纪的老作坊、老窖池,有遗存至今的,都被他们小心翼翼地保护起来。
欧杰实在不需要为没有保护好老厂房而耿耿于怀。毕竟,一个响亮的名称,产品就已经成功了一半,但它是品牌建设中的一个环节。而追溯历史,讲述故事,也都是品牌建设中的一环,而非全部——目前来看,仁怀酒企的“家长们”已经意识到了品牌的重要性,但缺乏正是品牌系统性建设。
欧杰应该是看到问题所在的,也清楚民营企业的短板——企业的经营、决策不能只集于“大家长”一身,企业的改变也不应只是名字的变更。他们需要得到更多的支持,首要就是引入更多、更专业的人才。
“我们已经在补缺失的这一块了,也在招人,希望能在一年之内解决大部分的问题。”欧杰这样说。
仁怀的传承
我们去的时候,欧杰的办公桌上摆满了酒样:有的是轮次酒,有的是勾调好的酒,有的是他自己厂里的,有的是外面送来的。数十种酒,都需要他亲自品评以定优劣,并给出改进意见的。几天之后,又换掉一批。
“浓香、清香、兼香我不懂,但是酱香你可以随便考我,”欧杰很自信,“不管是哪里酿的,南方、北方,或者仁怀、习水、古蔺,我能一口报出产地,(存放)有几年时间,是什么工艺、什么材料烤的,烤的过程中出了什么问题,值多少钱。不敢说百分之百准确,但八九不离十,我是实战出来的。当然,我家里也是有传承的。”
据说,欧家的祖上是重庆璧山迁到仁怀的移民。刚开始,欧家人只是做点小生意,到欧杰的爷爷、五爷爷辈,欧家已垄断了仁怀当地的天冬、杜仲、天麻等生意。
欧家酿酒是上个世纪三十年代左右的事,“烤酒渐渐有了名气,在这方圆百里内,仁怀的老人对我家酿的酒都有印象,在当时也是供不应求,长年不够卖。”
欧杰的父亲开办酒厂,也是重新操持祖业了,“父亲会酿酒,解放前还帮过爷爷、五爷爷烤酒。”1983年,欧杰父亲合伙建酒厂的时候,他也才14岁。就是那样一个年纪,家里既有传承,也跟着酒厂的师傅学。那位酿酒师傅叫汪德全,曾是茅台酒厂的老酒师。
他也试图把这门手艺传给儿孙。“小儿子三岁的时候,我就让他品酒。”品酒不是喝酒,欧杰把不同的酒各自倒入酒杯,又倒出来,只让杯子沾点酒香,再把杯子放在回风炉上烤。酒精挥发后会留有余香,欧杰让他分辨哪个杯子更香。
“他对酒很敏感,现在是省级白酒评委。”欧杰对两个儿子极其严厉,却很宠小孙女。他要抽烟,但怕烫到小孙女,打她出生后还把烟戒了很长一段时间。这大概就是所谓的“隔辈亲”。小姑娘三岁左右,一看到大人倒酒,就知道杯中为何物。
可见,仁怀人对酒精的热爱是刻在骨子里的,当然酒的氛围在这个家族中也很浓——家承相继,师徒相承,仁怀酒的传承便在日常的潜移默化中悄然进行着——尽管欧家人酒量不高,甚至年三十开的一瓶酒,可能到正月十五一家人都还没有喝完。
来源 | 糖酒快讯(ID:tjkx99)
本文为【糖酒快讯】原创文章,欢迎转发、分享,未经授权禁止转载或改编,如需转载请后台申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