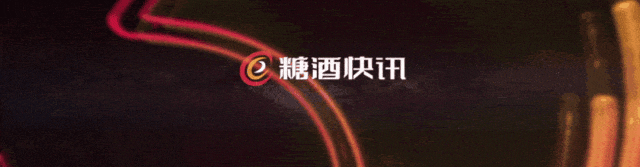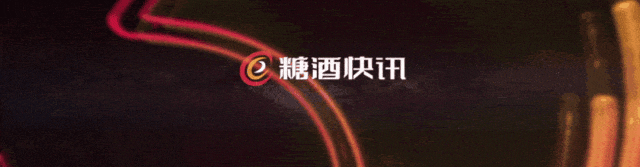
文 | 秦柯
1991年,刚刚在设计界声名鹊起的原研哉为完成他职业生涯中第一单威士忌包装,只身远渡重洋,来到苏格兰高地考察。其时威士忌市场整体萎靡,就连最大的托马汀(Tomatin)蒸馏厂的当家人麦克唐纳也打不起精神来,他对设计师说的最乐观的一句话是:“……不过……以后中国人该开始喝威士忌了。”

世事的确如他所料,此后不久中国人果然开始喝威士忌了,并且喝出了一条漂亮的,远远优于全球市场的上升曲线。
在大约二十年的时间里,苏格兰也成为最大赢家,从芝华士到麦卡伦,从调和到单麦,几大品牌交替领跑,牢牢把控着超过90%的市场份额。
直到2015年前后,「日威」逆民族情绪潮流几乎一夜之间生成热词,且以其近乎变态的“稀缺性”在高端消费群体中备受追捧。
中国市场上,日本威士忌25%的年增速远远将欧美对手抛在身后,尤其是在拍卖行等超高端奢侈品领域的标杆表现,严重挤压和威胁着麦卡伦、皇家礼炮等苏格兰品牌的现实与未来。
也许是近邻的表现,打开了我们的想象力与自信心。进入21世纪的第三个十年,「国产威士忌」便作为一个崭新话题从业内到业外开始逐渐升温、蔓延。近两年随着崃州、大芹、叠川等先行者陆续突破从投入到产出的周期临界点,它们的品牌和产品也通过种种渠道渗透消费者的视野与味蕾。
最近一些数据认为,国产威士忌的本土份额已经来到两位数,增速更是高达50%。而我认为,威士忌在中国,无论是消费市场,还是酿造产业,依然只是在经历“从0到1”的过程,此时数据中心论意义非但不大,还易误导,观察思考其战略趋势,定性比定量重要。
要讨论国产威士忌究竟是明日之城还是海市蜃楼这个问题,首先需要讨论威士忌在中国市场究竟能否真正的发芽生根,进入物种级序列。
这一点,葡萄酒的近年表现,颇值得我们反思借鉴。
今年有个触目惊心的数字在坊间流传,说葡萄酒份额只剩高峰期的15%,进口酒从风光一时无两到今天一地鸡毛,国产品牌从销量到利润更是呈现崩盘式下滑——要知道,这可是一个与中国现代工业亦步亦趋,经营了百年以上的成熟行当。
依我个人对十几年前进口葡萄酒风潮起落的观察,作为第一批“世界公民”的80后海归是其中主要推手,走向落寞的原因或许错综复杂,若取最要害处,则是因其自以为是的消费审美,与当下中国社会酒饮核心场景的需求特征严重偏离而遭到“遗弃”。与此同时,习惯了“随行就市”的国产葡萄酒自然也就难逃宿命。
那么,只有二三十年历史的威士忌与葡萄酒有怎样的可比性呢?
从推手身份特征来看,最早一批入局者之间还是有相似之处,我接触过几个四川、山东地区威士忌酒厂创始人,无一例外都有着留洋背景,我定义为“由爱好者开创”。他们虽不像当初“葡萄酒达人”们那样遍地开花,但资历、能力、实力等系统性的规模与厚度,却是前者不能同日而语。
产业际遇来看,与迎头遭遇茅台爆发、酱香狂飙淹没与压制的红酒风潮不同,威士忌崛起于中国酒饮核心消费场景正在发生彻底变革的当下,极有可能因恰逢世纪一遇的需求分化时代,从而登上未来消费者的酒单中心。
另外,从消费者血脉中对酒精饮料的偏好来看,很少有市场像中国由白酒这样的烈性品类占据统治地位的,因此当消费分化来临,相比白兰地或其他烈酒,高酒精度加上谷物原料的品类基因,也同样让威士忌处于有利的竞争位置。
国际竞争层面,地域冲突带来贸易摩擦不断,关税战争大概率会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影响其他强势产区品牌稳定、安全地进入和经营中国市场,这无疑也是给国产威士忌借机生根发芽,积累竞争力赢得了宝贵的时空窗口。
保乐力加和帝亚吉欧分别在国内布局酒厂,不能不说与其经历了前一轮贸易战影响之后采取的应对策略有关,同时也说明威士忌并不像葡萄酒那样,在品质上对产区风土有着过强的依赖。顺便提醒大家注意,两家巨头对厂址的选择——峨眉山下、洱海之源——与我们国产企业更愿意落地于啤酒、白酒、黄酒等酿造业产区不同,它们更靠近人文与人流的地标,这似乎在表明一种对威士忌的不同理解,某种程度上佐证了帝亚吉欧那条经典法则:“酒精度越高,文化属性越高”。
综上,不管从行业内部的结构演变与发展趋势审视,还是从外部环境的气候氛围与动态方向考量,国产威士忌以明日之城姿态矗立市场的客观条件确乎是存在的,甚至是充分的。
到此可见,能够影响国产威士忌去实现这一时代壮举的阻碍因素,就只可能来自于行业及企业的自身行为。由于商业竞争天然的残酷性,这些阻力的存在也绝不会以我们的美好愿望和进取意志为转移。那么时至今日,这些因素及其带来的风险是否已经显现,我们应该如何建立起针对性的认知,从而为寻求规避与突破打下基础呢?
请大家也容我再想一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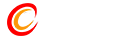
) APP客户端下载
APP客户端下载
 柯力度
柯力度